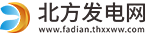
提要:16世纪初至17世纪中后期传统上被认为是英国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时期,英国普通民众在此期间遭受了普遍的贫困。20世纪80年代以来,英国史学界对“过渡时期”的贫困问题有了进一步的研究。这些研究成果和一些具体史实表明,英国这一时期的贫困远没有以往史家所描述的那样严重,而且由于生产发展和济贫制度的建立,使可能出现的严重贫困得到了缓解。同贫困相关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也显示了人们对贫困的理解是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
费边主义政治经济史学家R.H.托尼认为,贫困是资本主义的共生现象;资本主义的兴起导致了对农民土地的剥夺;而且,新兴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道德观改变了传统社会对穷人的态度,使他们遭受前所未有的冷遇和迫害。“新马尔萨斯主义”史学家从一个不同的角度肯定了托尼的估计。他们认为,随着1500年至1650年间英国人口的增长,雇佣工人的实际工资收人大幅度下降,生活水平严重恶化。人们一直把16世纪初至17世纪中后期的这一段时间看成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时期,因此,自托尼以后,英国普通民众在“过渡时期”遭受了普遍贫困的看法俨然成为定论。但是,20世纪70—80年代以来英国史学界“修正主义”盛行,托尼和“新马尔萨斯主义”史学家的学术正统受到挑战。D.M.帕利泽认为,16、17世纪英国人口增长并没有导致“马尔萨斯危机”;相反,他认为随着这一时期物质富裕程度的普遍提高,穷人的生活状况也有所改善。保罗-斯莱克从比较的角度指出,“值得强调的是,近代早期英国遭受的贫困要比许许多多其他社会轻。即使在饥荒时期,它的程度也远没有14世纪以及今天某些非洲和亚洲国家那样严重。比较人口情势表明,l7世纪后期法国农民比我们这一时期(都铎、斯图亚特王朝统治时期——引者注)任何时候英国雇佣工人和茅屋农更接近于勉强佣口的生活水平。”那么,以往史学家是否过高估计了英国“过渡时期”贫困问题的程度?如果果真如此,历史事实同他们的推导之间为什么存在如此之大的差距?本文将缕析英国学界对贫困问题的研究,并结合具体材料和有关贫困的宏观知识背景,展示英国“过渡时期”贫困的实况和人们对这一问题的不断变化的看法。也许只有如此,方能理解人们为什么对“过渡时期”的贫困问题倾注了如此多的注意力。
一
何谓贫困?这是学术界长期争论的问题。经济学意义上的贫困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在19世纪的讨论中,贫困是绝对的,以生存为标准的,其中最有影响的是英国改良主义者西博姆·朗特里在1901年出版的关于约克镇贫困问题调查中提出的“基本贫困(primarypoverty)”概念。所谓生活在基本贫困状态的家庭,是指那些“总收入不足以获取维持纯粹体能所需的最低数量的生活必需品的家庭”。在这里,“最低数量的生活必需品”主要是指食物。60年代中叶,为美国社会保障局工作的莫利·奥申斯基将“恩格尔系数”,即食物消费支出在家庭和个人消费支出中所占的百分比用于贫困问题研究,调整了衡量贫困家庭和个人的收入标准。彼得·汤森提出了更为弹性的贫困概念即影响深远的相对贫困论。相对贫困论改变了二战后流行的“资本主义消灭了贫困”的观点,使人们认识到“丰裕社会”的贫困。但是,相对贫困往往搀杂着人们对贫困现象的主观判断,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森认为,“相对贫困分析方法只能是对绝对贫困分析方法的补充而不是替代”。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英国“过渡时期”的贫困问题研究是在托尼、克里斯托弗·希尔的影响下进行的,他们采用的是社会学家的不平等方法,主要关心的是资本主义带来的财富占有不均现象。托尼、希尔的研究是理论分析性的,所用资料多为16、17世纪的社会批评家,如休奇·拉蒂默、罗伯特·克劳利和约翰·黑尔斯等人的言论和著述。实证性研究是由社会经济史学家w.G.霍斯金斯开启的,他试图根据政府1524年征收补助金(thesubsidy)时所作的财产估价,以及1522年的前期财产状况调查推算出生活在贫困状况中的人口比例。在理论上,那些年工资收入少于1镑,或拥有动产的价值少于1镑的人属于免税对象,他们在估价时被登记为“n,即“零”或“一无所有”。霍斯金斯将这些“一无所有”者看作是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穷人。按照他的统计,这一时期英国城市人口中1/3因“一无所有”而被免税,其中某些城市的免税比例更高,比如,在1522年考文垂的前期调查中一半左右的人口被登记为“n.r。除此之外,达到交税标准的人口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是交纳最低额度税金的工资收入者。因此,霍斯金斯估计“在16世纪20年代,足有2/3的城市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或非常接近贫困线”。
在很长时期,霍斯金斯的结论一直为史学界所普遍接受。他的方法也被用来分析保存更为完整的17世纪60—70年代的“炉灶税”(thehearthtax)记录。按照当时的规定符合以下两个条件的人可免交“炉灶税”:一是其居住的住宅年值1英镑或1英镑以下、拥有不动产1英镑或1英镑以下以及拥有动产10英镑以下者;二是因为低收入已免交教会税和济贫税者。据史学家统计,免交“炉灶税”的人口比例在30%一40%之间,同16世纪20年代初免交“补助金”的人口比例大致相等。除了政府的税收记录之外,格雷戈里·金的“1688年英国各类家庭收入和支出估算表”也是史学家的重要佐证。金将当时的英国家庭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收人大于支出,他称之为“使本王国财富增加”(increasingthewealthofthekingdom)的家庭,另一类是收入不敷支出,“使本王国财富减少”(decreasingthewealthofthekingdom)的家庭。其中前一类共511586户;后一类849000户,这类家庭包括雇佣工人、茅屋农、贫民、普通水手和士兵等。除此之外,还有3万没有家庭的无业游民。史学家通常将金统计表中人不敷出的家庭和没有家庭的无业游民算作穷人,他们占了英国当时人口的大半。综合上述各种材料,A.B.贝尔在1983年出版的一本关于都铎、斯图亚特王朝时期贫困问题的小册子中宣称:“可靠的税收记录表明在16世纪20年代和17世纪70年代1/3—1/2的人口生活在或接近于贫困状态。到本时期末,格雷戈里·金估计‘使本王国财富减少’的(家庭)总数高达3/5。因此从都铎王朝开始到斯图亚特王朝结束这一时期,英国有一支贫民大军,(他们)可能占全国居民的大多数。”
采用不平等方法的史学家提供反映当时穷人实际贫困状况的证据不多,因为在他们看来不平等和贫困的联系几乎是不言自明的。霍斯金斯说那些被免税的人口“没有任何可见的谋生手段”;w.T.麦卡弗里说:“极度贫困是一半以上人口的命运”;约翰·伯内特说:“在‘辉煌’的伊丽莎白一世时代,少数人享受着前所未有的富裕和奢侈,与此同时,几乎一半人口时刻徘徊在饥饿和赤贫的边缘。”即使在被列举出来的少量证据中也有不少可存疑的地方。比如,基思·赖特森和戴维·莱文在对特林村的研究中为了说明1550年至1650年间平民的贫困化过程,用了两条材料。一是已故茅屋农里查德·赛泽和妻子留下的动产清单。1622年赛泽去世时留下的财物包括两头耕牛、一头壮猪、一个旧柜子、工具、钱袋和衣物等。三年后他妻子去世时留下的财物更是少得可怜。其中床上用品包括一个旧床架、两床毯子、三床被单和一个旧的羽毛长枕,厨房用品包括一张小桌子、一条长板凳、两个柜子、一个装有羊毛的小橱、两个罐子、两个水壶、一把烤肉叉、五个木碟、六个白锻碟、一把火钳和一个揉面钵,衣物只有一件长外衣、两条围裙、一顶帽子和一双木底鞋。此外,还有户外奔跑的几只鸡。另一条材料来自一个在1623年冬偷吃了他人一只羊的名叫罗伯特·怀特黑德的人的供词:“(我)是一个很穷的人,有一个妻子和七个小孩,(我们)饥饿难熬”。但是,寡妇和家大VI阔的家庭可能只是穷人中的穷人,并不具备赖特森和莱文认为的代表性意义。
二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开始用经济学方法分析英国过渡时期的贫困问题,社会史学家的结论受到了置疑。索罗尔德·J.特朗鲁特认为和通常一样,当时人是从不平等的角度看待贫困问题的,他们所说的“穷人”是相对意义上的,而不是霍斯金斯等人认为的是生存意义上的。斯莱克认为免税者并非真的一无所有,他们只不过因为财产不多被估产人忽略罢了。查尔斯·菲西安一亚当斯对考文垂的研究表明,那些在1522年征税估产时被登记为“n的人口中相当一部分(17.2%)养有家仆,他们并非真正贫困。根据1523年该城的人VI统计,他计算出当时考文垂实际的贫困人口只有20%,而不是霍斯金斯估计的一半或2/3。
采用经济学标准的史学家认为政府的税收记录只是记载了财产的不平等,而非贫困。他们认为相对于政府的税收记录,英国市政府所做的贫困人口统计更为可信,因为该统计的观测点是穷人实际的生活状况。根据目前所能见到的6个城市的贫困人口统计(见表1),1557年至1635年英国穷人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分别为5%到20%一25%,远低于根据免税人口统计出来的穷人数。即使被市政府统计出来的贫困人口中,真正低于生存标准的穷人又只占少数。比如1570年诺里奇22%的人口被统计为穷人,接受救济者只占其中的1/4。斯莱克因此认为当时英国需要社会救济才能解除衣食之忧的赤贫者只占总人口的5%,但在经济危机时期可能上升到20%。
有关英国穷人食物和营养状况的直接证据有两种,一是当时人的记述,二是济贫机构留下的穷人饮食量规定。在1577年首次出版的《英国叙事》一书中,威廉·哈里森说英国富人吃小麦面包,穷人吃黑麦和大麦面包。但在荒年,许多穷人不得不吃由蚕豆、豌豆或燕麦制成的面包,而这些杂粮通常只用作马饲料。后一种情况似乎并不常见。在1623年灾荒时期,诺福克郡的治安法官报告说,当地穷人制作面包时不得不在大麦面粉中加进荞麦,由于他们以往很少吃这种面包,因此他们“显得很不喜欢食用”。哈里森还说在他生活的年代,富人吃的水产品、肉食和野味丰富多样,牛奶、黄油、干酪“现在被普遍认为只是下等人的美味食品”。穷人也吃肉,不过数量少得多。金估计,在1688年英国的550万人口中,270万人,即一半左右的人经常吃肉;44万个因为贫困而免交教会税和济贫税的家庭(合176万人)“每7天吃肉不超过2天”;另40万个要接受救济和施舍的最穷的家庭(合120万人)“每周吃肉不超过一次”。从这些资料中似乎可以看出,尽管同富人相比穷人吃得很差,但他们还是有吃的,并没有挨饿。
清教牧师理查德·巴克斯特1691年为英国贫苦佃农所写的陈情书可以证实这一印象。他说贫苦佃农比领主家佣仆吃得还差,佣仆跟着主人大鱼大肉,“可怜的佃户每周吃上一片晾干的咸猪肉就满足了,一些能杀头牛的人,偶尔吃上一小块晾干的牛肉,足以使他们大快朵颐。”他还说他们舍不得吃自家养的猪和鸡,自家产的蛋和水果,因为要用它们卖钱交租。他们还要卖掉最好的黄油和奶酪,留下脱脂干酪、脱脂奶和乳液凝块给自己和家人吃。尽管如此,他仍然承认这些并不足以损害他们的健康。
各种济贫机构,如慈善收养所(hospita1)、劳动救济所(workhouse)和教养所(houseofcorrection)留下了较为详细的穷人饮食量规定。这里是一份1687年4月(伦敦)圣·巴塞洛缪慈善收养所管理机构通过的饮食表:星期天:10盎司小麦面包,6盎司煮熟的无骨牛肉,1品脱半牛肉汤,1品脱热酒、稀粥,3品脱(每桶)6先令的啤酒;
星期一:10盎司小麦面包,1品脱牛奶糊,6盎司牛肉,1品脱半牛肉汤,3品脱啤酒;
星期二:10盎司面包,半磅煮熟的羊肉,3品脱羊肉汤,3品脱啤酒;
星期三:10盎司面包,4盎司干酪,2盎司黄油,1品脱牛奶糊,3品脱啤酒;
星期四:饮食量同星期天,1品脱加米牛奶糊;
星期五:10盎司面包,1品脱糖泡软食,2盎司干酪,1盎司黄油,1品脱水煮稀粥,3品脱啤酒;
星期六:饮食量同星期三。
不过慈善收养所接收的穷人主要是老弱病残者,在需要从事体力劳动、而且往往是重体力劳动的教养所,穷人吃的东西更多。比如1589年萨福克郡贝里的圣·埃德蒙兹教养所中穷人每日的饮食包括453克面包,1.136公斤粥,227克肉,1.136升啤酒。在“吃鱼日”不吃肉,而是吃400克海鱼和302克干酪。
按照朗特里的营养学方法,卡罗尔·沙玛斯试图将济贫机构中穷人的食物数量转换成卡路里。按照她的计算,1589年贝里教养所的穷人日摄入热量2884卡路里,1687年圣·巴塞洛缪慈善收养所的穷人日摄入2323卡路里。因此,她认为按照今天的标准,济贫机构的食物足以维持人静态的生存,但不足以从事重体力劳动。罗伯特·于特的估计比沙玛斯更乐观。按照他的换算,1500年至1800年包括英国在内的西北欧济贫机构中穷人日摄入热量近3000卡路里,而20世纪一个从事中强度体力活动的人需要2900-3200卡路里。不过,前工业时期欧洲人的身材小一些,他们所需要的热量也因此少一些。
当代学者采用的恩格尔系数也被应用到16、l7世纪英国贫困程度的分析之中。按照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标准,恩格尔系数在60%以上为贫困,50%一60%为温饱,40%一50%为小康,40%以下为富裕。事实上,霍斯金斯是最早采用这种方法的,他说在这一时期“一半至2/3之间的人口是靠工资为生的劳动者”,而且,“工人阶级在饮食方面足足花去他们收入的80%到90%”。如果霍斯金斯的估计成立的话,当时英国的大多数人口无疑生活在“极度贫困”之中。但即使是金,一位被当代史学家认为有夸大当时贫困程度之嫌的人,也未得出如此悲观的结论。他在1697年对其估算结果作进一步说明时,将英国人V1分为三类,他说:“我发现最穷的一类总开销只有每年3英镑或每天2便士,在饮食上花去2/3或略高于每天5法寻(旧时值1/4便士的硬币或币值——引者注);中等的一类人头总开销每年7英镑,在饮食上每年花去4英镑;富裕的一类人头总开销每年50英镑,在饮食上的开销少于1/3”。照此计算,英国穷人的恩格尔系数为67%,远低于霍斯金斯估计。
沙玛斯试图根据英国郡治安法官公布的工资规定推算出当时雇工饮食开支在他们工资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工资规定是以日计的,其中既有包伙食的,也有不包伙食的。沙玛斯的推算方法是从不包伙食的工资中减去包伙食的工资,得出伙食所需的费用;然后用伙食费用除以不包伙食的工资,得出伙食在雇工工资收人中所占的百分比。
表2中所划分的5个时期,1420—1514年是一个例外。由于“黑死病”的影响,当时的英国仍然人12:1稀少,劳动力紧缺,使得雇工的实际工资保持在较高水平。由于收人较高,他们用于饮食支出的比重因而较低,只有43.4%。除此之外,在其余四个时期雇工用于饮食的支出在51.9%和55.0%之间。按照恩格尔系数,16、17世纪的英国雇工似乎已经达到了温饱水平。但是沙玛斯的计算有两个明显缺陷,一是她在饮食消费中只计人了雇工本人的消费,但在通常情况下,雇工的工资还要用来养活妻小。二是沙玛斯是按日计算的,但是,雇工并不是每天都劳动,因此,还要匀出一部分用于非劳动日消费。约翰·康洛斯认为雇工一年劳动可能不超过275天。如果将275天的收人用于365.25天的开支的话,他们用于食物的开支将上升到70%。沙玛斯本人已经意识到计算的缺陷,不过她认为尽管工资只是用于支付雇工个人,而不是整个家庭,但雇工家庭通常还有其他收人。她根据戴维·戴维斯和弗雷德里克·艾登18世纪80、90年代提供的数字,认为在通常情况下雇工户主的工资还占不到家庭总收人的2/3。唐纳德伍德沃德和约翰·沃尔特等人的研究表明,16、17世纪的雇工,包括那些被认为同农业经济分离最彻底的建筑工人,都保有一小块地。他们通常还享有使用公用地的权利。“对于许多(家庭)来说……工资只是收人的一部分。”基于上述考虑,沃尔特在自己的论文中引用了沙玛斯的计算结果,用以修正霍斯金斯过分悲观的估计,但他承认,“毫无疑问,关于(穷人)收人和支出的事实根据还需要更严格的考查”。
从16、17世纪英国饥荒爆发的情况亦可推晓当时的贫困状况。安德鲁·B.阿普尔拜的著名研究表明,1587—1588年、1597年和1623年英国西北部的坎伯兰和威斯特摩兰曾遭受过严重饥荒。在这些年份许多堂区的死亡人数比通常高出2倍、3倍甚至4倍。有些堂区登记人员还在死亡登记簿上注明了死者的死因,从中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死亡同饥荒的联系。比如格雷斯托克堂区的登记人员记载1623年1月下葬了“一个孤独无助的可怜人”;3月掩埋了“一个饿死的可怜讨饭娃”和“一个饿死的可怜讨饭男孩”;5月,“詹姆斯·欧文,一个可怜的要饭小伙……死于……极度悲惨中”,同月,还死了“一个毫无生活来源的穷人”。阿普尔拜同时指出这些饥荒是地区性的,对经济发达的南部地区影响较小;而且即使在易受饥荒影响的西北边远地区,饥荒的程度也在逐渐减轻。在稍晚发表的一篇关于英、法饥荒对比的文章中,他进一步指出法国从1630年至1709年遭受了严重生存危机时,英国“在这一时期没有生存危机”。阿普尔拜开创性的研究得到了剑桥人口和社会结构课题组更为详实的研究成果的印证。通过对英国人口死亡率的逐月分析,他们发现当法国、布拉班特和苏格兰因欠收出现死亡危机(mortalitycrises)时,英国却没有类似的变化。他们得出了同阿普尔拜一致的结论:“因此,17世纪中叶以前似乎有两个英格兰:一个畜牧和边远的英格兰;另一个从事农耕但具有高度专业化程度的英格兰……”由于出产谷物,加上发达的交通运输网络。使得后者,即英格兰东南部较少受歉收的影响;前者则相反。不过1623年以后英格兰西北部也摆脱了歉收的影响。阿普尔拜和剑桥课题组的研究人员并不是最早得出这一结论的人,早在1662年一位名叫约翰·格朗特的人就宣称英国死于饥饿的人极少。据他对伦敦近20年死亡登记的研究,在229250死亡人口中,死于饥饿的不超过51人。
三
英国“过渡时期”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出现了财富占有不均现象,16、17世纪的人口压力又在一定程度上恶化了雇佣工人的经济状况,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可以缓解贫困问题的条件和因素。其中有些是技术方面的,比如阿普尔拜认为英国之所以能够较早地摆脱16、17世纪的生存危机,主要是因为英国扩大了春播作物,如燕麦、大麦的播种面积并提高了它们的产量。由于不受或较少受冬季气候的影响,春播作物的价格稳定。因此,当越冬作物小麦和黑麦因严冬歉收时,穷人可以靠价格低廉的、平时只用作马饲料的燕麦、蚕豆和豌豆度过饥荒。因此,阿普尔拜说:“在法国,穷人由于过高的价格完全从谷物市场上被排挤出去,因而他们挨饿;英国穷人则以相当合理的价格得到可替代谷物,因而,他们既没有挨饿,也没有死于与此相关的营养不良。”
阿普尔拜提出的技术原因无疑是重要的,但生产的发展,尤其是生产的实质性发展——劳动生产率提高可能意义更为重大。费边主义者似乎认为社会财富的总量是固定不变的,因此一部分人之得必然是另一部分人之失。事实并非如此。在经历了中世纪晚期的“封建主义危机”之后,领主对农民的地租剥削减轻,与此同时,在大陆欧洲发展起来的直接税,如法国的人头税(taille),并未在英国出现。英国的税收是以补助金名义征收的,是非常规性的,而且税率也很低。因此,相当一部分农业剩余保留在直接生产者——农民手中,它们往往被以这种或那种形式投入到农业再生产之中。16、17世纪的英国农民比他们中世纪的前辈拥有更多牲畜。马克·奥弗顿和布鲁斯·M.s.坎贝尔利用2000份庄园账簿、3000份遗产清单对混合农业发达的诺福克郡进行了量化分析,发现14—17世纪该郡单位面积上的牲畜密度翻了一番。在莱斯特郡的威格斯顿村,普通农户有3匹或4匹马,它们被用于拉车、犁地和耙田。该村首富威廉·阿斯特尔有12匹马、20头牛和100只羊。农民还投资于改良土壤、兴修水利等方面。
早在1967年埃里克·克里奇就指出,由于新技术的出现,如草场一耕地轮换、水灌草地、排干沼泽、人工施肥、选种以及引进代替休耕的肥田作物等,英国农业在组织形式尚未发生大的变化的情况下,使粮食产量翻了一番。尽管他的某些具体观点,如由于过分强调16、17世纪的“农业革命”而贬低18、19世纪的农业进步,在学术界引起争议,但他对于这一时期农业发展的基本估计却得到了广泛的认同。C.G.A.克莱在1984年出版的一部带总结性的关于16、17世纪英国经济史的教科书中写道,根据诺福克和萨福克的资料,估计英国小麦的亩产量从15世纪的8—9蒲式耳上升到17世纪后期的14—16蒲式耳,增长了75%左右。大麦和燕麦上升的幅度可能更大。加上其他因素,如改两田制为三田制、引进肥田作物等,16、17世纪英国农产品总量增长了两倍半以上。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史学家在克里奇等人的研究基础上前进了一步。他们将“生产率”区分为“土地出产率”和“劳动生产率”两类,认为16、17世纪英国农业进步的主要表现还不是土地出产率,即粮食亩产量和总产量的增长,而是农业劳动者人均生产粮食数量的增长。G.克拉克根据统计资料,对1300年和19世纪中叶英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进行了比较,发现在此期间英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人均净产出指数由0.38上升到0.95,远远高于同一时期的欧洲大陆国家。克拉克认为这一变化主要发生在1600年之前。罗伯特·C.艾伦持类似看法,他认为英国历史上经历了两次农业革命:一次是17世纪“约曼的农业革命”,另一次是18世纪“领主的农业革命”,即圈地运动;无论在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还是在提高劳动生产率方面,前一次革命的影响都远远大于后者。
由于资料的限制,克拉克选择的比较对象是19世纪中叶,而不是他所要强调的16、17世纪。因为13、14世纪英国有大量庄园账簿,19世纪有丰富的官方和非官方调查报告,这两类资料可以用来计算当时劳动投入和产出的比例,但在16、17世纪类似的资料却极为有限。正因为如此,克拉克和艾伦的估计是可存疑的。事实上,马克·奥弗顿就坚持认为英国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发生在18世纪,尤其是18世纪中叶以后。
除了前面提到过的资本和技术因素外,还有一些因素有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比如在16、17世纪市场经济的刺激下,英国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大大提高;16、17世纪的英国农民,尤其是“约曼”农经营的土地面积远远大于中世纪的小农,有利于劳动力充分使用,减少隐性失业;宗教改革废止了中世纪频繁的宗教节日及其庆典活动,使得生产者可用于生产活动的时间大大增加。当时人已意识到在他们生活的年代生产率有很大提高。威廉·哈里森在《英国叙事》中写道:“毫无疑问,它(指英国土地——引者注)就在我们亲身经历的日子里变得比过去丰产的多,因为在获取的推动下,我们的农民变得比过去更能吃苦,更有技巧和更加细心”。
英国财富增长的主要受益者是新兴的社会中间阶层,如约曼农、独立的手工工匠、中小商人,但普通民众也在一定程度上受益。16、17世纪英国雇佣工人的实际收入情况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但有迹象表明并不太低。16世纪前期考文垂雇工的日工资最低不低于3便士,木匠帮工的日工资为10便士,菲西安一亚当斯认为,在正常情况下考文垂的实际工资水平,“至少足以使雇工生活保持在高于真正的生存贫困线以上,帮工生活则远远高于生存贫困线”。17世纪末已经有人抱怨英国雇佣工人工资太高,以至于影响到该国的制造业。已故雇工的动产清单表明当时部分雇工是富裕的,比如16世纪60年代去世的莱斯特郡雇工理查德·斯潘塞遗留下来的动产价值达32英镑18先令8便士,其中18英镑零6便士是别人欠他的债务。他有一处茅屋及其周围的3—4英亩地;此外,他还有在公用地上放牧的权利,他在那里养了20只羊、6头牛,还有2—3头猪和6只母鸡。
除生产发展外,当时人对贫困问题的高度重视以及政府采取的行之有效的济贫措施是“过渡时期”贫困问题得以缓解的另一重要因素。贫困在中世纪早已存在,但一直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这与罗马天主教的影响有关。在中世纪贫困被看作是一种“神圣状态”,穷人被看成是“上帝(受难)的肢体和他本人的代表”,是“上帝的嗣子”,“上帝的至爱”。受贫困崇拜思想的影响,中世纪的欧洲出现了一批自愿贫穷者——托钵僧和职业乞丐,他们走村串巷,以乞讨为生,成为当时欧洲一道奇特的风景线。罗马天主教还宣称施舍可以洗清人的罪,因此,贫困是不可能也不应当清除的,因为它为成千上万渴望拯救的人提供了施舍的对象——穷人。
这种状况在15、16世纪发生了变化。由于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兴起,贫困问题变得比以往更加严峻,迫使人们不得不正视它。当人们用世俗的眼光重新审视贫困时,它没有了以往神圣的光彩。意大利人文主义者认为贫困有损人的尊严,阿格里帕·道比涅说:贫困“使人丢人现眼”。16世纪上半叶,当受到人文主义熏陶的英国人突然“发现”他们面临的贫困问题时,反应尤其强烈。黑尔斯惊呼:“贫困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普遍过”。英国人文主义者还将贫困与社会动乱联系起来,弗朗西斯·培根在《论叛乱和动乱》时说:“叛乱之源有两种:多贫与多怨。有多少破产者就有多少动乱拥护者,这是确定无疑的。
从16世纪20~30年代开始,英国的市政官员、慈善家就尝试解决贫困问题的各种途径和方法。在总结地方经验的基础上,英国政府于1598年、1601年颁布了著名的《济贫法》。通过征收济贫税并在基层堂区设置济贫官员,从而建立起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济贫制度。1793年,兰开夏郡首席治安法官托马斯·巴特沃思·贝利自豪地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穷人得到过像我们这里如此充足的供养。我们每年都征收数额巨大的资金,用于养活他们……”贝利的说法并非夸张。据估计,1783—1785年间英国年平均用于济贫的开支占国民总收入的2%,领受救济的穷人达到总人口的10.9%,足以覆盖英国生活在生存标准线以下的穷人。
看来英国过渡时期的贫困问题远没有以往史学家描述的那样严重。尽管英国在这一时期经历了社会分化和不平等,但由于生产发展以及近代济贫制度的建立,使可能出现的严重贫困问题得到了缓解。费边主义史学家在论述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兴起的同时强调“过渡时期”的不平等,后世的史学家力图展现这一时期贫困的真实状况,而关注贫困问题的其他人文和社会科学学科更是将这一话题拉得更远。也许贫困问题并不在于贫困本身,而在于人们对社会异质性的敏感。
向荣,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关键词: